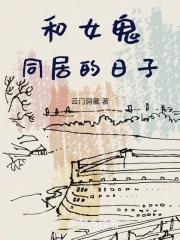麒麟中文网>末世:带着系统养男宠(NPH) > 152发情贺锦延微h补昨天第四更(第1页)
152发情贺锦延微h补昨天第四更(第1页)
他顿了两秒,没听见说停的声音,便再次扬起手。
又是“啪!”一记脆响。
贺锦延不敢留力,几下之后,就比路元清亲自扇他时还肿,从皮肤下隐隐渗出一片血丝。
“好了。”路元清这才站起身,不轻不重地随意踢他一脚,“戴上再过来,脱干净。”
贺锦延如蒙大赦,顾不上自己整个下半身都又酸又疼,边勉强站起来,边将面罩匆匆带回去。
他跟在路元清后面,一瘸一拐地走进浴室,脱裤子时,手都在发抖。
膝盖始终没得到过休息,像灌了水泥一样疼。
再加上刚才,为了上叁楼,他又不肯找人搀扶,不得不使用能力。
连带着药物生效,直到现在,阴茎在锁里仍半硬着,顶端挨在带电的小圆罩磨蹭。
戴着锁熬过这段时间的激烈战斗,贺锦延已经被锻炼得相当能忍痛,仍会被刺得时不时绷紧大腿肌肉。
要害一暴露在空气里,他便立刻喘息起来,扶着瓷砖地跪到路元清面前,受尽折磨的下体甚至抖了抖,涨大一分,从锁顶端的小孔里淌出期待的清液。
贺锦延浑身一抖,再仰头看她时,眼底已经有些发红:“我……”
然而,下一秒,他的满怀期待,只迎来一束兜头浇下的水。
冒着热气,却毫无温情。
路元清拿着花洒,短暂地晃了一秒神。
这个场景,让她有些回忆起最开始,刚把“贺少爷”从f栋强行掳回家的时候。
也像现在这样,在无害的水流下,在她居高临下的注视里,男人狼狈地发抖,倨傲的灵魂被她亲手浇熄,却无处可逃。
她像在冲刷一头牲口似的,从头到脚,把贺锦延淋了个透湿。
这才微微撇开花洒,弯腰打开那个禁锢他的锁。
没等贺锦延伸手,路元清又再次直起身,用水流打断他的挽留。
——和之前,还是有点不太一样。
现在的贺锦延,知道她有意亵玩自己,便连下意识闪躲的动作都不敢做得太大。
他浑身肌肉都绷得死紧,在水流下铺陈开流畅有力的线条,到底还是控制住自己,顶着强力的水柱,慢慢恢复成跪坐的姿势,分开大腿,低下脑袋。
这具身体已经被浇透了,两粒乳头在冲刷下颤巍巍地胀红,底下那根性器也被逼着再度勃起。
它好像要一口气把被束缚的痛苦都发泄在此刻一般,青筋毕现,硬得格外气势汹汹,挺到几乎贴住贺锦延自己的腹肌。
每次路元清改换花洒角度,水柱从新的方向落下时,它都会被砸得轻抖一抖,再生机勃勃地涨得更红一些,牵连出贺锦延好几声压抑的粗喘。
然而,就在他已经快控制不住自己声音的时候,水温,却突然降了下去。
冰冷如雪,倾注在他脑袋上,从头浇下。
带走刚升腾起的满室热气,也带走贺锦延无法说出口的绮思。
濒临沸腾的血瞬间冷却下去。
他不敢躲,硬咬牙受着,直到胯下的东西彻底耷拉下去,在水流下无精打采地摇摆,路元清才关上龙头。
她把花洒随手扔在旁边,丝毫没修饰语气的不耐烦:“我给你能力,是要你办事的,别成天跟个发情的狗一样。
“以前衣服穿不住,现在连裤子都穿不住了?”
贺锦延头发全都湿漉漉地耷拉下来,往下滴着冰冷的水,说不出半个字。
路元清叹口气,拿出条浴巾,扔到他脑袋上:“别光顾着委屈了,现在能好好听我说话了吗?”
长时间分离积蓄的期待和思念,都在她的冷淡面前化为云烟。
又随着浴巾落下,飘飘摇摇地回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