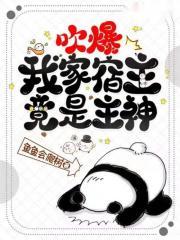麒麟中文网>人在大商,持刀斩天 > 第三十五章 破落村庄奇人怪棺(第1页)
第三十五章 破落村庄奇人怪棺(第1页)
西岐城外二百三十六里处。
姬旦从亥时出,一口气行出几个时辰,直至此地已到三更时分。
月朗星稀,荒无人烟。
姬旦纵身从马背之上约跃下,不忘将脖颈面罩往上一拉再拉,等到彻底兜住自己英俊的容颜这才罢休。
露出一双狭长的眼睛警惕的朝身边看去,现四下无人,这才放下心来。
从怀中掏出一张地图,凭借从小荷那里临时恶补来的知识,借着清冷月光,勉勉强强辨别出三个字来:“锁儿郎!”
父亲西伯侯姬昌巡狩归来,就于此处遇刺!
锁儿郎所处地,在贯穿整座西秦雍州北部的秦山曲折之处,沟壑密布起伏跌宕,平原少而多深山,往来仅有一条坑坑洼洼乡间泥路供人通行。用一句山大沟深穷乡僻壤形容在不为过。
姬家列代先祖励精图治,重农业并重商业,施仁政引贤才,引得九州之内无数逃而来的荒难民同胞,在西秦雍州境内能够分得属于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田园去安身立命。
虽此处土壤贫瘠,可耕种面积少,水资源匮乏,可那居无定所流离半生之人,终有一块立足之地可遮风挡雨,无不感激涕零自此扎根下来繁衍生息。
民以食为天。
水资源匮乏?
那就举全村之力,广修水渠,将深山当中的溪水引到田垄当中,浇灌绿荫!
土壤贫瘠?
那也无妨!
大清早,迷迷糊糊的大半小子,就被老爹从睡梦当中揪起耳朵从床上拽起来,一口气背着自家小子来到田中,挺着腰身对先来上一泡酣畅淋漓的晨尿再说。
即便吃坏肚子,肠胃当中犹如跑马一般格外难受,也舍不得到茅厕解决,那得到自己田垄里边一泻千里!
往往光着屁股的两个大汉,即便碰在一起,隔草相望顿时心领神会,也不尴尬。
“哟,来施肥呐!”
“呵,您也不是嘛!”
起初仅有十来户的锁儿郎,却在短短十年之年,一举扩张到二百来户,农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,鸡犬相闻自得其乐。
一位偶然路过此地的教书先生修建起了村中的第一所私塾,问身边弟子,你们长大后的目标是什么呀?
孩子们十有八九的回答说,争取多吃饭多喝水,努力将自家那黄土,给养成种啥长啥的黑土地!
于是乎,先生有感而一句打油诗。
山大沟深志气短,锁得儿郎尽白头!
此言一出,锁儿郎之名口口相传,至于这个村子最初的叫法,却被人逐渐忘记。
可就是这样一处充满生趣的村子,却在两年前逐渐凋零,以至于成了现在这样破落荒废之地。
村里的老顽固坚持己见,在村子西南处划分一块荒山,按照姓氏不同界定各家祖坟,
一路逃荒逃难于此的可怜人,或突然暴疾,或饥肠辘辘活活饿死,或山贼打劫脑袋搬家,总之外乡人,均不得埋入锁儿郎划分的祖坟当中。
于是老学究和乡绅长者,又在村落西北角的荒山下划分了一块乱葬岗。
无论天南海北客死异乡之人,裹上一张草席,潦草葬于此处便算完事。
锁儿郎四周荒山并无多少植被,远远看去光秃秃一片,大风一吹黄土漫天飞扬。
黄土松软留不住老天爷慷慨的馈赠,滚滚雨水顺流而下,卷起沿途泥浆碎石,冲出道道狰狞的缺口。
进而引山体滑坡,本就被被裹了一张草席乱葬于此的羁客旅人,被泥沙包裹添堵在了裂缝洼地当中。
有村志记载说,五年前那场特大山洪从天而降,似有移山填海之威能,从山根底下冲出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,村民一拥而上争相抢夺,可惜现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,最后也就见怪不怪,任其散乱荒野。
可自此之后,村庄怪事不断。
四年前,村里的二愣子,说他在乱葬岗月亮底下瞧见一大堆密密麻麻的人影。
村里李大娘家的黄犍牛打到荒山吃草放牧,不出一个时辰,体型偌大的黄犍牛轰然倒地,报备完官府,全村人眼巴巴等着吃牛肉,剥开牛皮,却未现一滴血液。
正值青壮的黄犍牛,已然被活活吸死!
三年前,已经死了两个多月的王大头突然返家,四肢僵硬目光呆滞,只认得自己不会下崽的老婆。
原本是村头有名悍妇的王大头老婆,却连吓的跟个鹌鹑一下,瑟缩在门内,连大气都不敢出上一下。
两年前,不知是何物,在张乡绅蹲茅坑时被抓烂了半边屁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