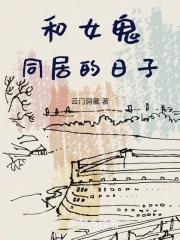麒麟中文网>渡我九重天 > 第26章(第1页)
第26章(第1页)
山谷之中一座木凉亭掩在花丛里,偶有蝴蝶在花间翩然起舞,景色极盛。
嫪婼躺在凉亭之下,两旁挂下的轻纱,遮掩亭中一二,偶有风起,才能看见亭中情形,古琴焚香,墨画高挂,屏风轻掩,竟似中原做派。
宋听檐在亭中,贺浮站在其后。
嫪婼身后两个老者站着,显然是形影不离。
嫪婼一身红纱层叠,越显肤白艳美,手撑着额,芊芊玉手拿着几页纸垂眼看,片刻后才放下,看向前面长身玉立的宋听檐,“敢问公子,何以只有这么几页?”
“文章繁长,还容在下细细写来。”宋听檐四两拨千斤,若清风朗月,叫人无可反驳。
嫪婼视线在他玉面上落了几瞬,“公子为何不坐下一叙?”
宋听檐依旧平和,“三日之期尚短,时间不许在下久坐。”
“原是如此,时间本就尚短,公子若觉得不妥,我可以等,不必如此生急。”
宋听檐依旧有礼有节,轻轻松松推了回去,“多谢族长,只是在下祖母等不得。”
嫪婼闻言慢慢起身,赤足落于地上,脚踝处刻着繁复花纹,红纱裙往上而开,没入大腿之上,修长纤细的腿行走间,忽隐忽现,叫人观之心神荡漾。
贺浮见状当即别开视线,面色微红,颇有些不敢多看。
嫪婼美目盯着宋听檐,缓步往宋听檐身旁走去,在他身旁慢慢绕了一圈,视线落在他身上,窄腰长腿玉面,上下皆是一一观察。
她唇角微勾,眼神如同一个钩子,话间皆是勾引,“中原公子都似你这般长身玉立,容色惑人?”
她说着抬手鲜红指甲的手如灵蛇游动,正要抚上他的胸膛。
宋听檐却平静一笑,随手挡过嫪婼欲抚上来的手,仿佛枝上落叶掉落衣上,他随手拂去一般不在意,“中原人杰地灵,似我这般自是繁多。”
如此绝色美人,他却没有半点动容,那勾引之意是丝毫没放在眼里。
夭枝忍不住啧了声,眉头皱得可深。
身旁洛疏姣猛地抓过脚下生出来的杂草,恼火至极,正欲低声叫骂,却听身旁夭枝啧啧啧了几声,似难言至极。
她转头看向夭枝,却发现她神情比她还要急,她一时愤慨,“你……你难不成也要喜欢我簿辞哥哥?!”
夭枝看了她一眼,疑惑,“很多人喜欢他?”
洛疏姣面上一红,不经意间暴露了自己的心思,她轻咳一声,“那是自然,似簿辞哥哥这般人中龙凤能有几人?”
夭枝闻言只觉叹息,她极为认真地观察宋听檐,见这般半点不近女色,太过离谱,直摇头,“看来药不够猛。”
洛疏姣没听明白,松了手中的杂草,“什么药?”
夭枝闻言未语,自然是要替宋听檐保密,做这行她还是知道规矩的,她看着嫪婼,“这女子可是宋公子喜欢的风格吗?”
洛疏姣瞬间被转移了注意力,忿忿不平看去,“怎么可能!簿辞哥哥常年礼佛,品行端正,怎会喜欢这样扭来扭去的人!”
常年礼佛……那不是常年清心寡欲吗?
夭枝陷入沉思,只怕是不好治啊。
那边嫪婼第一次有男子这般拒绝她,瞬间没了好心情,她转身回到矮榻上躺下,看了他半响,笑起来眼里却有冷意,“公子可别忘了三日之约,三日后若交不出来,这诓骗之罪你们可未必能承受。”
这以上对下的威胁于宋听檐这般出身的贵子自是从来没有过,更何况是这荒僻一处的所谓族长。
宋听檐唇角微弯,面上依旧分辨不出情绪,“第三日必然能给族长一个满意的答复。”
嫪婼见他这般肯定便也不再为难,她伸手指向前面桌上摆着的琴,“你们中原人附庸风雅,公子这般气度应当也会弹琴,可否弹上几曲与我听听?”
这可是明目张胆的拿人当乐子了。
洛疏姣听见这话气得不轻,“什么蛮荒之地的女子,竟敢将簿辞哥哥作乐人看待!”
夭枝在一旁摸了摸下巴,这事应该没关系罢,虽说此人娇贵了些,但弹弹琴也不会少根指头。
她开口没太在意,“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嘛,她要听,随意弹弹就好啦,我们到底是有求于人。”
洛疏姣猛地转头看向她,“这是折辱,簿辞哥哥是何等身份,她又是什么东西让簿辞哥哥弹琴!”
夭枝见她激动,开口提醒,“你再大声点,我们可以一道下去跳舞。”
洛疏姣当即哑声,忍不住哭腔,“此等蛮荒小族怎能如此折辱?”
夭枝看了眼亭中,站起身安慰道,“既如此,我们先回去罢,不看你簿辞哥哥被折辱的场面就不算折辱了。”
洛疏姣闻言生生一噎,硬是接不上半句话来。
这是人话吗?天下还有这样的人,真是活久见,且还让她碰见了。
夭枝转身离开,却听宋听檐依旧平和开口,“中原世家子弟不通弹琴取乐之举,家中皆有乐师。”
“是吗,那公子会什么?”嫪婼显然不高兴了,美艳的脸上笑意全无。
“取乐之事,一概不会。”宋听檐平静回道。
这胆子是真大,这回答在这种吃人族里真真是不要命的。
“呵。”嫪婼冷笑出声,已然知晓此人是骨头又硬又傲气,不过到了她这,怎样的傲气,怎样的硬骨头,最后都得乖乖跪下求饶,而她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驯服的过程。
她忽然又笑,盈盈开口,“公子回去写医经罢,早些写出来,我也早些给你药。”
这话说的倒是合乎情理,只是这般语气可不像是真的要给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