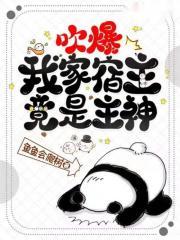麒麟中文网>眉山苏氏,苏允最贤 > 第八十三章有点东西(第1页)
第八十三章有点东西(第1页)
除此之外,苏辙还将庄子骂朋友惠施的事情给苏允给讲了讲。
这事儿呢是庄子的朋友惠施在大梁做国相。
有一次庄子想要去看望他。
结果呢,有人以讹传讹告诉惠施说,其实庄子过来看你是假,想取代你的宰相才是真的。
惠施一听,那还得了,于是,马上派人搜捕庄子,后来,庄子实在看不过了,就主动出来见惠施。
并且对他说,南方有一种叫凤凰的鸟,听说这种鸟呢,非常特别,不是梧桐树,它不落下休息,不是竹子的果实,它绝对不吃,如果不是干净的泉水,那么它宁肯渴着,也不喝上一口。
有一天呢,一个嘴里叼着死老鼠的猫头鹰,从它面前飞过。
这只猫头鹰唯恐凤凰抢它的食物,于是,它的嘴里一直出“喝喝”的怒斥声。
苏允听完之后大笑不止,没想到庄子这般这样一个清心寡欲仙气飘飘的人,骂起人来竟也是这般不客气。
有意思,真有意思。
苏辙见苏允兴致满满,心里也是开心,不怕你没有志向,就怕你没有兴趣,兴趣是最好的老师,只要有兴趣,那就有懈可击!
于是,苏辙更加卖力的将课程变得有趣,不断地引经据典,将诸多圣人有趣的事情拿出来说,将自己毕生所学糅合其中,竟是将一本原本枯燥的孟子讲得趣味横生。
几天时间一晃而过,苏辙意味犹尽的停止授课。
苏允十分感慨,若是前世能遇到这样的语文老师,何愁文言文学不好?
经过这几天的授课,苏允也是当真见识到这个时代的文人的积累到底有多恐怖,而他们所学习的这些经义又是何等的奥妙。
后人学文言文,就学里面的翻译、大意,能够将文言文翻译成现代语言,就算是过关了,但这个时代的经义学习,了解大意只是基础,贯通里面的微言大义才是关键。
比如说这孟子,后世读懂大意就算是学了,这会儿的学懂须得将孟子核心的仁义二字彻底读懂,还得贯彻孟子的执政理念,这还不够,苏辙还将如何运用这些理念的实例给讲明白才算是完成。
也就是说,你光学个大意,连基础都不算,你还得明白孟子的执政理念,这才才算是打牢了基础。
而你要学懂学透,却是需得知道怎么将这些理念运用于实际。
苏辙为官多年,多年来一直贯彻孟子的【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】的民本思想。
苏辙将这些年他为官的经验与孟子的思想相互对照,跟苏允讲清楚他为什么要反对青苗法,又为什么要劝谏宋仁宗,在地方上为官时候又是怎么【省刑罚,薄税敛】的。
苏辙以他多年为官的经历,以及这个过程之中反过来去思考孟子的执政理念,而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是极为宝贵的。
而这些经验通常都会被当做传家之宝,除非是自家子侄或者是亲传弟子,否则都不会被传授的。
这些东西也就是只有那些官宦世家才有的东西,而苏辙却是毫不藏私传给了苏允。
几天的时间,苏允不仅学会了孟子一书,还知道了大量的为官经验,不知道是不是苏辙为了让苏允不排斥入仕,因此刻意美化官场的一些事情,苏辙将为官为民的事情讲得特别引人入胜。
苏允当然明白苏辙的意思,他自然也不反对,他不愿意为官不是因为叛逆,而是他觉得自己尚且救不了自己,哪里谈得上救他人。
达者兼济天下,穷者独善其身嘛。
原本苏允觉得入仕可能会极大消耗他的精神力量,但在苏辙教了孟子之后,苏允忽而觉得,或许进入官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?
所谓小隐隐于野,中隐隐于市,大隐隐于朝,或许公门之中好修行?
或许以后若有机会,大约可以试试?
苏允学得开心,其实苏辙教得也开心。
教学相长嘛。
苏辙没有用这种角度来教人,因此教学的时候不得不穷搜枯肠,将自己毕生所学、经历、思考都拿出来,用一个全新的角度去总结讲述,在这个过程之中,学的人固然收获颇丰,但教的人领悟更多!
而教学之中,交流是必要的,一问一答之中,两人的思想自然会有所碰撞。
苏允是什么人啊,他是个后世人,后世人的一个普通想法,拿到宋朝来,可能便是颠覆三观的暴论!
苏允在学习中,会拿着后世的看法去对照,因此也会有诸多不解,而这些不解拿出来问苏辙,苏辙常常有大开眼界的感觉:这样也行?
其中两人争论最多的是王安石变法,毕竟这是当今大宋最为核心的政治问题。
苏辙兄弟因为新法而屡遭贬谪,因此苏辙时时都在思考这些新法,既有思考其中利弊的想法,或者是有着寻找其中破绽,给新法致命一击的想法。
无论是出自于哪种想法,终究是绕不过时时思考新法这一关的。
日有所思,那讲课的时候自然而然便将其拿出来举例了。
苏允虽然没有入仕的想法,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,畅谈国事吹牛逼,本来就是人生一大乐事,而且还能够跟苏辙这个当初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亲历者一起吹牛逼,那可真是太爽了!
于是苏允将后世看过的一些关于王安石变法的看法拿出来就是吹,至于对错苏允是不管的。
吹牛逼只讲气势,管什么对错嘛。
反正自己只是一介草民,对象又是苏辙这个叔父,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嘛。
于是,苏允只是吹牛逼,但苏辙却是真真切切地领悟到了更多的东西。
苏辙一开始也是以为苏允在吹牛,但听着听着,却是大大吃惊起来:这小子,里面的真东西可真不少啊!
苏允认为他只是在吹牛逼,但他的那些想法是根据结果来倒推的东西,事后诸葛亮嘛,推出来的东西未必都是对的,但肯定比身在局中的人看得更加清楚。
苏允讲的那些东西,可都是后世的专家们用后世的经济学政治学归纳出来的东西,是越宋代的,甚至用高屋建瓴来形容都不为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