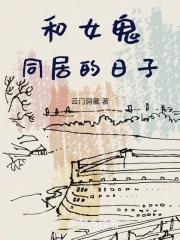麒麟中文网>惜少年 > 第2章(第1页)
第2章(第1页)
道理邱尚都懂,若是将邱尚放在陈涛的位置,他想必也是一样,明明他们都是那样的亲近,结果所有的事只有自己被瞒着,任谁都不会舒坦。
可邱尚还是不敢贸贸然去找陈涛,只能盼着陈涛早些冷静,这一等就等了近十日。
陈涛的确不好过,他高高兴兴的去上朝,准备迎接顺利回朝的梁思凡,可却在朝堂上知道这么一桩惊天计谋,然后他发现,他亲近的人都对他伪装了。
只有张远道,只有他跟他一样,可后来他也不见了,原先如何辉煌的张家,现在只剩张远道的大哥苦苦支撑着,陈涛恨自己什么都帮不上张远道,天下百姓不知道,皇帝早已被梁思凡秘密处决,因此张远道才会失踪,他同时失去了父亲和爱人,没有谁比他更难过。
管家原本圆润的脸,这十来日皱成了苦瓜,甚是愁苦:“老爷,你就别再喝了,这些日子你把自己当成了酒坛子那样灌,身子会承受不住啊!”
陈涛不予理会,仍旧咕噜咕噜的喝。
管家道:“我知您心里难受,可也得顾着身子,您这样您这样有个万一可如何好?”
他见陈涛还是不听,便大胆的去抢他的酒坛,却被陈涛一手挥开:“夜深了,你不用守着,回去睡吧。”
桌上空了两个酒坛子,满屋的酒味,他却清醒得很。
心脏像是被针扎那样疼。
管家还想开口,却被一人抢先打断:“尚学”
管家微愣,稍即一脸欣喜,苦了多日的脸终于见到救星般,他看向门口,邱尚披着烛光站着:“邱公子,总算把你盼来了,你快劝劝老爷吧。”
邱尚迟疑片刻,还是迈开步子走了进去,他对屋子里的味道熟悉的很,却是皱皱眉,没说什么:“有我看着,你放心回去休息。”
管家哎了声,又看了眼仍默不作声的陈涛,无声的叹口气,退出了房间。
门一关,陈涛就冷声道:“不请自来?邱公子未免太自觉了些。”
不理会他的冷嘲热讽,邱尚将倒在桌子上的酒坛一一扶好:“老师担心你,让我来看看。”
说到楼清,他更沉默了,于此同时,心中更痛:“我一个外人,竟劳驾楼先生担心。”
邱尚道:“你何必自轻自贱,老师从未与你疏远。”
“安慰的话少说,邱尚,我现在没心情与你说这些事,看也看了,好走,不送。”
他若是强硬点,陈涛反抗不过他,可邱尚就是没舍得下手:“别喝了,我让小峤给你备了水,擦擦身子,早些休息。”
陈涛冷笑:“邱尚,不过一场同窗,你也管的太宽了些。”
邱尚抿紧了唇,甚至连手都握紧了,他应该不管不顾,将人敲晕,省得听伤人心的话,这样可以省了很多事,可他就是不愿,他知道他来会面临什么,却哪怕是千疮百孔,都想问个答案:“从十四岁到及冠,你我相识六年,这些在你眼里,是否真的只是一场同窗?还是连当日的生死与共,也全都不重要?”
“相识再久也不过是欺骗,邱尚,阳关道与独木桥,我们都不可能走到一块,转身,免得自取其辱。”
刹那间,邱尚的脸色一片苍白,经过这几个月的调养,他的身子圆润了许多,面容也恢复年少的清秀,可如今,硬是给陈涛说白了。
邱尚多想此时陈涛是醉了,哪怕丝毫的不清醒,也好让他自欺欺人下去,可他的眼神邱尚熟悉,再清醒不过。
邱尚终于明白,连自欺欺人,也得有借口才行。
邱尚就杵在那,一动不动,仿若一尊雕像。
陈涛也没心情再理他,重新拿了酒坛,大口大口的灌,肚子涨了,酒劲上来,陈涛才摇晃着身子要去解手。
到底还是担心,邱尚及时扶住了他摇摇欲坠的身子,他的腿站久了,有些麻,可此刻都给对方占据了,全都感觉不到。
陈涛站稳身子,将人拂开,又跌跌撞撞的走。
恰好小峤让人布置洗澡水,见陈涛这样,赶紧扶住他:“少爷。”
陈涛定睛看了看,见是小峤,才沉声道:“我要解手。”
小峤见他已半醉,又看了眼身后的邱尚,挨不住陈涛督促,扶着人去了。
邱尚趁此命人将酒坛收走,打扫干净,又开了窗,吹走酒味。
等邱尚做完这一切,小峤扶着人回来了。
“少爷,我给你擦了身子再睡。”
陈涛不应,却抬手脱了衣裳,接过帕子洗脸。
邱尚一直看着他,其实应该转身就走的,他很明白,不管什么道,他们都不能走到一块,留下来是自取其辱,可看着他的身影,邱尚就觉得自己的脚被定住了,好像先前忽略的麻一股脑的全回来了。
小峤将擦洗干净的陈涛扶上床,见邱尚还在,便问道:“邱少爷,你是在这住下还是怎样?”
邱尚看向小峤:“不了,我待会便回去,你先休息,我和尚学说几句话。”
免得小峤麻烦,邱尚拒绝了。
小峤应了声,端着水走了。
邱尚走到床边,看着床上闭目躺着的人。
他喜欢陈涛,从十四岁到及冠,从初恋到深爱,不长不短,正好六年。
六年了,答案很清晰,可他不甘心,陈涛凭什么否定他?
六年,就算是欺骗,可那是怕他知道。
床上的人因着喝了酒,脸颊泛红,他本就长得英俊,如今散着发的模样,给那抹红一衬,竟有几丝妖媚。
像小猫扑住蝴蝶那般,邱尚给他按住了心。
这是他离陈涛最近的一刻,他知道,一旦机会错过,就再也没有了,他和陈涛,会像他说的那样,从此东西南北,各不相干。